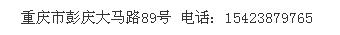
8
春天降临了。
乡村的春天总是和仪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像我们无双镇,春天一露头,就有拜谷节,播洒谷种的前一夜,每个村子的老老少少都要带上祭品,去本村最大的一块稻田里供奉谷神;拜谷节过去没几天,就该是迎接灶神爷的日子了,猪头是不能少的,还有小米渣,听老人们说,天上是没有小米渣的,人间全靠这点东西留住他老人家了;把灶神爷安顿好,就是晒花节了,太阳公公和花仙一起供奉,因为有两个神仙,供品自然不能少,蜂蜜、白米,干菊花,还有圆圆的玉米饼。太阳还没有出来,一庄人早就遥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把供品摆放妥贴了,等那抹血红一上来,大家就整齐的磕头作揖,好听的话也会说不少,庄稼人没野心,就是祈求有个好年成。
晒花节刚过,土庄又热闹了。人们槐花串似的往焦三爷的院子里跑,扛凳子搬桌子的。遇上闲逛的路人,就有人招呼:“焦三爷传声了!”,路上的人一听,一张脸就怒放了,随即融入队伍。往焦三爷的院子迤逦而来。
土庄人等这个盛况的日子已经很久了。
无双镇的唢呐班每一代都有一个班主,上一代班主把位置腾给下一代是有仪式的,这个仪式叫“传声”,不传别的,就传那首无双镇只有少数人有耳福听到过的“百鸟朝凤”。接受传声的弟子从此就可以自立门户,纳徒授艺了,而且从此就可以有自己的名号,比如受传的弟子姓张,他的唢呐班子就叫张家班,姓王,则叫王家班。总之,那不仅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荣耀,它似乎是对一个唢呐艺人人品和艺品最有力的注脚,无双镇的五个庄子都以本庄能出这样一个人为荣。
这个仪式最吸引人的还不是他的稀有,而是神秘。在仪式开始之前,没有人知道谁是下一代的唢呐王。所以,焦家班所有的弟子都是要参加这个仪式的,连他们的亲人都会四里八乡的赶来参加,因为谁都可能成为新一代的唢呐王。
人实在太多了,师傅的院子都装不下了,于是屋子周围的树上都满满当当的挂满了人参果。我和我的一班师兄弟坐在院子正中间,两边是我们的亲人,我父母还有两个妹妹都来了;我的师弟蓝玉坐在我的旁边,他的家人也来了,比我的父母还来得早些。他们的脸上都是按捺不住的期待和兴奋。
屋檐下有一张八仙桌,八仙桌的下面是一头刚宰杀完毕的肥猪。此刻,这头猪是供品,仪式结束后,他将成为全土庄人的一顿牙祭。猪头的前面有个火盆,火盆里的冥纸还在燃烧。师傅坐在八仙桌后面。他一直在闷着头抽烟,师傅的烟叶是很考究的,烟叶晒得很干,吸起来烟雾特别大。很快,师傅的一张脸就不见了,他的半截身子都隐在一片雾障中,像一个踏云的神人,我竟然生出一些隐约的幻意。
良久,师傅才站起来,四平八稳的拄灭手里的烟袋,对着人群,平伸出双手往下压了压。喧闹的人群瞬间就安静下来。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师傅发话了。
“我快要吹不动了,可咱们这山旮旯不能没有唢呐,干够了,干累了,大家伙儿听一段还能解解乏。所以啊!在咱们这地头唢呐不能断了种。我寻思了好久,该找一个能把唢呐继续吹下去的人了!”师傅咳嗽了两声,停了停,下面又开始有响声了。这个时候我偷偷的侧目看了看蓝玉,我发现蓝玉也在偷偷的看我,他的嘴角还淌着一些笑。四目相对,我的脸刷就红了,像是心里某种隐秘的东西被戳穿了似的。蓝玉的脸没有红,他的脑袋抬得更高了,像一只刚刚得胜的大公鸡。我就升起一些不快,想还没见底呢,咋知道水底是不是石头?又想想,我的这班师兄弟里,也只有蓝玉最适合了,他人精灵,天分高,也勤苦。反正最后是他我也不会惊奇的。最后我觉得我那几个师兄也可怜,为什么师傅不全给传了呢?那样就整齐了,人人有份,个个能吹百鸟朝凤,焦家班、蓝家班、游家班,还不响亮死啊!
师傅又开腔了:“我这几年收了不少徒弟,大大小小的,个个都有些活儿,出活也带劲,没给吹唢呐的丢人。”顿了顿师傅接着说:“我们吹唢呐的,好算歹算也是一门匠活,既然是匠活,就得有把这个活传下去的责任,所以,我今天找的这个人,不是看他的唢呐吹得多好,而是他有没有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一个把唢呐吹进了骨头缝的人,就是拼了老命都会把这活保住往下传的。”师傅又咳嗽了两声,对旁边的师娘点了点头,师娘过来递给师傅一个黑绸布袋子。师傅接过来,小心翼翼的从里面抽出来一支唢呐。远远的我就感觉到了这支唢呐该有些年龄了,铜碗虽然亮得耀眼,却薄如蝉翼,杆子是老黄木的,唢呐的杆子一般就是白木,最好的也就是黄木,能用这样色泽的老黄木制成的唢呐,足见它的名贵。乡村人一般是见不到这样的稀罕货的。
“这支唢呐是我的师傅给我的,它已经有五六代人用过了,这支唢呐只能吹奏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就是百鸟朝凤。现在我把它传下去,我也希望我们无双镇的唢呐匠能把它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师傅举着唢呐说。
院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只听见我的师弟蓝玉的喘息声,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师傅手里的那支唢呐。我相信这一刻的土庄是最肃穆的了,这种肃穆在了无声息中更显得黏稠,我最后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了。
我侧目看了看我的师弟蓝玉,他紧缩着脖子,脑袋花骨朵似的。慢慢地,他的脖子被拉长了,成了一朵盛开的鲜花,花朵儿正期待着雨露的降临,焦虑、渴望在稚嫩的花瓣间涌动着。蓦然,盛开的鲜花枯萎了。几乎就在一眨眼间,正准备迎风怒放的花儿无声地凋谢了,花瓣起来了一层死灰,花杆儿也挫短了半截。这朵刚才还生机蓬勃的花儿,转眼间铺满了绝望的颜色。悲伤一下从我的心底涌起来,我的师弟蓝玉,迅速的在我眼睛里枯萎,他的目光慢慢的转向了我,我能看懂他的眼神,有不信、不甘、绝望,当然,还有怨恨,可我看到的怨恨很少,很稀薄,星星点点的。
这时候我的父亲,水庄的游本盛在旁边喊我:“你呆了,师傅叫你呢!”
父亲的声音像耍魔术的使用的道具,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9
蓝玉走了,披着一身绚烂的朝霞,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去了。我站在土庄的土堡上,看着他的身影逐渐变小变淡。太阳明天还是要升起的,可我却见不到我的师弟蓝玉了。蓝玉在我的生命里出现和消逝都突然得紧,仿佛那个落雨的日子,蓝玉就该出现在我的面前,又仿佛这个炫目的黄昏,他本就一定要离去。
昨晚的晚饭很丰盛,有师娘做得最好的土豆汤,师娘做土豆汤是要放番茄的,番茄在无双镇不叫番茄,叫毛辣角,毛辣角又是土庄特有的小个毛辣角,樱桃样。师娘把剁碎的毛辣角和土豆搅拌在一起,还放了半勺猪油,颜色血红,喝起来酸酸的,很开胃;另外,还有蓝玉最喜欢的灰灰菜,灰灰菜是凉拌的。我在水庄没有见到过这种野菜,蓝玉说他们火庄也没有。嫩嫩的灰灰菜在水里飞快的跑过一趟,晾干后凉拌,居然有鲜肉的味道。
饭桌上师娘不停地往蓝玉的碗里夹菜,一盘灰灰菜差不多都到蓝玉碗里了。蓝玉很得意,不停的对我撇嘴,还故意砸吧出嘹亮的声音。师傅吃饭是没有响动的,他每一个动作都很小心,在饭桌上你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直到他把一筷子灰灰菜夹到蓝玉的碗里,我才发现师傅一直都在饭桌上的。师傅的这个动作让我和蓝玉的嘴合不上了。要知道,焦家班的掌门人没有给人夹菜的习惯。他总是静悄悄的在饭桌上干他该干的事情,不要说夹菜,就是话也极少说的,有客人他也只是两句话,开饭时说吃饭,客人放碗时说吃饱。师傅看见了我和蓝玉的惊讶,就对蓝玉说,多吃点,这种灰灰菜只有土庄才有的。
我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在晚饭后终于得到了证实。
师傅照例在油灯下吸烟,蓝玉就坐在他的面前。
“睡觉前把东西归置归置,明天一早就回去吧!”师傅对蓝玉说。
蓝玉低着头抠指甲,不说话。
“差不多了,红白喜事都能拿下来的。”师傅又说。
“师傅,是我哪里没有做好吗?”蓝玉问。
“你做得很好了,你是我徒弟中悟性最好的一个。”
“那你为什么要赶我走?”蓝玉终于哭了。
“你我的缘分就只能到这里了!”师傅叹了口气说。
“蓝玉不要哭,没事就到土庄来,师娘给你做灰灰菜吃。”师娘也有了一窝子眼泪。
“我吹得比天鸣都好,天鸣能学百鸟朝凤,我为什么不能?”蓝玉咬着牙说。他力气太大了,把左手的中指都抠出血来了。
师傅眼睛一亮,忽然又暗淡下去了。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烟袋悬在嘴上,背着两只手离开了,走到门边才把烟袋从嘴里拿出来,回过头说睡吧,明天还有事情干呢!这话听上去是对师娘说的,又好像是对屋子里所有的人说的。
睡在床上,我有很多的话想对蓝玉说,可有不知道说什么好。一直到天亮,我们谁都没有说一句话。焦家班的传声仪式结束后,蓝玉很是难过了一阵子。没多久他就缓过来了,他对我说,只要还留在师傅身边,他就一定能吹上百鸟朝凤。我是相信蓝玉的,我知道师傅传我百鸟朝凤是因为我老实,不传给蓝玉是觉得蓝玉花花肠子多。其实师傅是不对的,蓝玉天分比我好,他确实是比我精灵了一些,可人精灵点有什么不好的呢?我打心眼里希望师傅能把百鸟朝凤传给蓝玉,我也这样对蓝玉说过,可蓝玉不领情,还说我挤兑他呢!
现在师傅要让蓝玉走了。我的师弟最后的希望也就没有了。
蓝玉走的时候就是寻不见师傅。蓝玉在屋子里找了一圈也没寻着,师娘说定是下地去了。蓝玉就在院子里给师娘磕了六个头,说师娘我给你磕六个吧,你和师傅各自三个,我一并磕了。师娘把蓝玉扶起来,眼泪就哗哗的下来了。蓝玉走了,背着一个包袱,狠狠的转了一个身,留给我一个瘦削的背影。
蓝玉不见了,师傅从屋子后面的草垛子后转了出来。我回头看见了他,他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我教你百鸟朝凤吧。
10
游家班到底是哪一年成立的我忘了。那年我好像十九岁,抑或二十岁?我经常在夜晚寻找我的唢呐班子成立时候的一些蛛丝马迹。暗夜里抽丝样出来的那些记忆大抵都和我的唢呐班子无关,倒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从记忆的缝隙里顽强的冒出来,堵都堵不住。
最深刻的当数我的堂妹游秀芝和人私奔。秀芝是我四叔的闺女,一直是个老实的乡下女娃,脸蛋一年四季都红扑扑的。见到生人就红得更厉害了。之前没有一点迹象表明她要离开生她养她的水庄。那个普通的早晨,我的四叔发现他的闺女不见了。一家人慌张的找了一天也没有寻着。后来有人告诉四叔,天麻麻亮看见秀芝和赵水生一起翻过了水庄后面的那座大山。赵水生是水庄赵老把的儿子,刚脱掉开裆裤就和他老子去了远方,听说是个大城市。秀芝读书的时候和他是同桌,受过他不少欺负,我还替秀芝揍过这龟孙子一顿呢!
无容置疑的,赵水生拐走了秀芝。
四婶哭了好几场,说姓赵的这几天跑过来和秀芝两个躲在屋子里嘀嘀咕咕,感觉就不对头,然后就骂姓赵的,骂完姓赵的又骂自个儿的闺女;四叔则是每日都杀气腾腾的样子,多次表态要活剐了姓赵的。一年后事情才出现好转。秀芝寄回来了一封信,信里说她很好,在深圳的一家皮鞋厂上班,一个月能挣半扇肥猪,还照了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个大水塘,比水庄的水塘可大多了。后来才知道,那不是水塘,是大海。
我很奇怪为什么我的记忆里都是和游家班成立无关的事件。为此我陷入了长时间的自责,并试图用记忆来缓解这种不安。可是在梳理属于游家班的丝丝缕缕时,却让我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中,因为这些记忆没有一丝亮色,相反,它像一面轰然坍塌的高墙,把我连同我的梦都埋葬掉了。
不知道出师四年还是五年后,师傅把他的焦家班交给了我。
那天师傅对一屋子的师兄弟们说:从今后,无双镇就没有焦家班了,只有游家班。一屋子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很茫然,手足无措。他们的眼神都带着笑,善良而温暖。可我却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我只知道今后这一屋子人就要在我稚嫩的翅膀下混生活了。我想起了六七岁放羊的经历,父亲把七八只羊交给我,对我说,给我看好了,丢了一只你就甭想吃饭。我特别害怕山羊漫山遍野散落的情景,总是希望他们紧紧的拢成一团。在路上我就和山羊们商量好了的,可一上了坡它们就没有规矩了,眼里只有茂盛的青草,哪儿草好就往哪儿奔,弄得我眼里尽是颗粒状的白。到回家的时候,这些白就更稀疏了。我那时除了哭真是没其他的好办法的。
而此时,那个叫游本盛的男人正挑着一对儿箩筐在水庄的山路上轻快的飞奔。他对遇见的每一个重复着一句话:天鸣接班了,今后无双镇的唢呐就叫游家班了。他说这句话时除了自豪,更有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在自己预言降临时的自负。
猝然而至的交接像一场成人礼,从那天起,我眼里的水庄褪去了一贯的温润,一草一木都冰冷了,那些整日滑上滑下的石头也变得尖锐而锋利。
11
游家班接的第一单活是水庄的毛长生家。
过来接活的是长生的侄儿。一进院子就给我父亲派烟,父亲把香烟吸得有滋有味的,一脸的幸福。这是他的唢呐匠儿子严格意义上给他带来的第一次实惠,滋味自然是与众不同的。
我刚从屋子里出来,父亲就冲着我喊:“八台哟!”
“我叔是啥人?别说八台,十六台也不在话下的。”接活的说。
父亲白了长生侄儿一眼:“你妈的x,哪有十六台?”
长生侄儿裂了裂嘴,说现在不是天鸣做主吗?自个儿造啊!别说十六台,捋出个九九八十一台也行啊!
父亲这回笑了,快意的猛吸了一大口烟,他从蹲着的长条木凳子上一跃而下,说:“那倒是。”
我点了师傅和几个师兄的名字,长生侄儿就蹦达着去通知了,走的时候又给父亲派了一支烟,父亲接过香烟说你龟儿子脚程放快些,晚上要吹一道的哟。
其他几个师兄都来了,师傅和蓝玉没有来,长生侄儿说他好说歹说说到口水都干了,师傅还是不来,只推说身子不太利索。我没有问他蓝玉为什么没有来。
我家屋子不大,寨邻来了不少,把一个院子堵得满满的,都想看看游家班的第一次出活预演。大庄叔也来了,父亲还单独给了他一条独凳子和一碗浓茶。大庄叔一脸的笑,说真没想到这唢呐班的当家人会是天鸣这崽儿,平时十棍子敲不出一个屁,吹起唢呐来还叫喳喳的呢!当年你爹说你能吹上百鸟朝凤老子还不相信呢,看来你游家真的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几个师兄话不多,一直笑,父亲给每个人都倒了一碗烧酒,还不停的催促说喝啊喝啊润润嗓子啊!
水庄的夜晚好多年没有这样热闹了。四支唢呐呜呜啦啦的吼。奏完一曲丧调,人群里有人喊说天鸣整一曲百鸟朝凤给大家听听。我说那不行,师傅交代过的,这曲子是不能乱吹的。人群又起来一阵轰,老庄叔把凳子往我面前挪了挪,说就整一段,给大伙洗洗耳朵,这曲子当年肖大老师走的时候我听焦三爷整过一回,那阵势真他奶奶的不得了,能把人的骨头都给吹酥了。我还是摇头,父亲站在我身后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儿吧,以后机会多的是,天鸣保证给大家吹。老庄叔看见父亲发了话,也站起来说对对对,不依规矩不成,以后听的时间还多,散了吧都。
人群散了去,我对几个师兄说,这是游家班第一次接活,不能砸了,再走几遍吧。
远远的就看见了长生,他头上顶着一块雪白的孝布站在院子边等我们。看我们过来,长生给每个人派了一支烟。自己也啜上一支。我说老人家什么时候走的?长生喷出一口烟,笑着说这个月都死三四次了,死去没多久又缓了过来,直到昨天早晨才算是死透。旁边一个老人干咳了两声,说长生,快行接师礼呀!接师礼就是磕头。长生回头看了看旁边的老人,说接什么卵师呀!天鸣和我啥关系?一起比过鸡鸡的。然后他回头看着我笑笑,我也笑笑。
我其实倒是很希望长生给我磕个头。长生比我大五岁,是个精灵货,个子也比我大,小时候放牛我没少挨他揍,揍了我还要我喊他爹,喊过他多少回爹我都忘了。我一直想着报仇的,慢慢长大了,懂事了,报仇这个事情也就丢到一边了。今天本来是个机会,可长生还是显示着他一贯的与众不同。算起来,长生算是水庄第一个穿夹克和牛仔裤的人,这几年水庄人都前仆后继的把庇护了自己几千年的土墙房推到了,于是水庄出现了一排一排的镶着白晃晃瓷砖的砖墙房。水生看准了这个变化,拉上一群人在水庄的河滩上搞了一个砖厂。现在水庄好多人都不叫他长生了,叫他毛老板。
长生给游家班的待遇充分展示了他毛老板这个称呼并非浪得虚名。一人一条香烟,比起那些一支一支扔散烟的人家户,这种一次性的大额支付确实让人快意,因为我从几个师兄接过香烟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像打了一辈子小鱼小虾的渔民,今天忽然就网起来了一头海豹。
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我的几个师兄在吹奏的时候是多么的卖力,我真担心他们用力过猛会震破手里的唢呐。特别是长生打我们旁边经过的时候,我大师兄高高坟起的腮帮子像极了他妻子怀胎十月时的大肚皮。
除了香烟,毛老板的慷慨还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润嗓酒,是瓶装的老窖;再比如乐师饭,居然有虾。那玩意通体透红中规中矩的趴在盘子里,连我都看得傻了,虾我听说过的,是水里的东西,我们无双镇好多水,可我们无双镇的水里没有虾,只有一汪一汪淡绿的水草。长生最大的慷慨还不是这些,而是看见我们卖力的吹奏时,他就会过来先给每个人递上一支烟,说别太当回事了,随便吹吹就他妈结了。
走的那天长生没有送我们,而是每人递给我们一把钱。大师兄说了,这是他吹唢呐以来领到的最多一回钱,二师兄在一边也说,钱是最多的一次,可吹得是最轻松的一次。
我捏着一把钱站在水庄的木桥上,木木的看着一庄子正起来的炊烟。
12
稻谷弯腰了,我去看了一回师傅。
又见到土庄的秋天了,一马平川的黄一直向天边延伸。
师傅刚下地回来。他好像更黑了,也更瘦了,裤管高高的卷起,赤着脚,脚板有韵律的扑打着地面,地面就起来一汪浅浅的尘雾。走到我的面前,他把手里的锄头往地上一拄,下巴挂在锄把的顶端,看着我笑笑,就伸出沾满泥土的手来摸我的脑袋。
“看你那双爪爪哟!”师娘嗔怪师傅。师娘也赤着脚,裤管也高高的卷起,正从屋子里往外搬凳子。
我把从水庄带来的东西拣出来放到院子里的木桌上。有师傅喜欢的旱烟叶子,烟叶是我到金庄出活时给买的,师傅说过无双镇最好的旱烟叶在金庄;还有腊肉,腊肉是我父亲烘的,颜色和肉质都好,带给师傅的是猪屁股那一段,在乡村人眼里,猪屁股是猪身上最珍贵的部分;此外还有母亲让我捎给师娘的碎花布,让师娘做件秋衣。
“来就来,还叮叮当当的带这样一大堆。”师娘总是要客气一番的。
我和师傅坐在院子里,这时候夕阳上来了,水庄就晃眼得紧。远处的金黄在晚风中奔腾翻滚,我都看得呆了。师傅指着远处对我说:“看那片,是我的,那谷子,鼓丁饱绽的。”我说我知道的,师傅就哈哈的笑说对对,你在的那阵子下过地的嘛。
我给师傅装了一锅刚带来的烟叶,师傅吸了一口,再吸一口,说没买准,金庄最好的烟叶在高昌山下,那片地种出来的烟叶才是最地道的,这烟叶儿不是高昌山下的。
“要吃人家饭,最后还要拉屎在人家饭盆里。”一旁剥蒜的师娘给我主持公道。
“前几天你二师兄来过一趟,说你们那边乐师钱出得很阔呢!”师傅往地上啐了一口烟痰说。
“不多的,就是有钱的那几家大方些!”
“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晚饭时辰,师傅搬出来一土壶烧酒。
十年了差不多,师傅一脸兴奋的说,火庄陈家酒坊的,那年给陈家老爷出活的时候到他酒房子里接的,没掺一滴水。
师傅在饭桌上照例没话,低着头呼啦啦的吃,间或端着盛酒的碗对我扬扬,这时候我也端起酒碗对着他扬扬,然后就听见烧酒在牙缝里流淌的声音。
我在土庄整整呆了三年,没见过师傅喝过一滴酒。其实师傅是有些酒量的,三碗青幽幽的烧酒倒下去,师傅的脸就有了猪肝的颜色。两个眼睛也格外的亮。
最让我惊奇的是那天师傅喝完酒后在饭桌上的话,那个多哟!比我在木庄听他说了三年的话还多。那天师傅说一些话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师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像一只老狼,两手撑着桌面,脸向我这边倾斜着,眼睛里则是血红的光芒。他说唢呐匠眼睛不要只盯着那几张白花花的票子,要盯着手里那杆唢呐;还说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最后我的师傅焦三爷终于扛不过他珍藏了十年的陈家酒坊的高度烧酒,瘫倒在桌子上了,他倒下去的那一刻,两只眼睛直直的看着说:
“有时间去看看你的师弟蓝玉吧!”
第二天起来,师傅师娘都不见了,我知道他们下地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规律得和日出日落一样的。我还是有些晕,走到屋外,院子里木桌上的筲箕里有煮熟的洋芋,这算是给我的早饭了。那些日子就是这样的,我和蓝玉每天早上都要为拿到大个的洋芋争斗一番的。
站在山梁上,我回头看了看土庄,它好像老去了不少,那些山,那些水,都似乎泛黄了。
13
马家大院看上去比五年前阔多了,楼房像个长个子的娃,几年光景就多出了三层。马家在木庄都习惯领跑了,还把后面的拉下一大截。老马家两层小平房起来了,木庄其他人家还在茅草屋子里忍饥挨饿,好不容易有了两层小平房,一瞧,老马家都五层了。木庄人总是在老马家屁股后面,怎么跑都跑不过。个中缘由除了老马脑筋好用以外,最主要的是老马有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娃子。几个娃出门早,据说中国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脚印。
可惜精打细算的老马还是耗不过病痛,六十不到的人,年前还背着手在木庄的石板路上检阅风景,年后就蹬腿了。四个儿子回来奔丧,每个人都有一辆小汽车,十六个轮子一码子停靠在木庄的石板街上,成了木庄人眼里一道稀有而复杂的风景。
游家班在马家大院里呈扇形散开。八台,也当然是八台。烟酒茶照例是不能少的,还有黄澄澄的糕点,放进嘴里又软又酥,上下颚一合拢,就化掉了。几个师兄都兴奋的交谈着,连平时话最少的三师兄都停不下口,他慌乱的说话,慌乱的把好吃的东西往嘴里扔,好几次该他的锣声响起了,他都还在为他那张嘴在奋斗。我有些火了,吼了他两声,没多久又听不见他的锣声了。
我忽然好惶恐。从我们进到马家大院起,好像就没有人白癜风的治疗办法北京哪个医院看白癜风比较好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处:网站地址 http://www.sohjm.com//kcyhl/110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