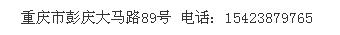兄弟深圳上车的时候,天就在下雨,到了西安,雨还在下。走的时候,因为匆忙忘记了带雨伞,但火车一停,我还是毫不犹豫跳下车,冲进了雨中。医院,只有两站路,在这个城市曾经经历过四年的大学生涯,非常熟悉。一路上无以名状的焦虑,让我不愿意在打的或者等待公交车的时候多耽搁那怕是一分钟,下火车后,想都没想就拔腿奔上大街。雨中的街道,宽阔阴暗。那些打着雨伞,匆匆行走在街道上的人和悄然滑过的车辆,无声无息,没有任何人注意奔跑在街上的我。往日喧嚣的都市,此刻如同一段正在播放的默片。我的耳朵里,除了自己胸腔煽动的声响,沉重的呼吸,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医院,冲进门诊大楼,大楼里乱糟糟摩肩接踵的人,乱哄哄如同马蜂一样的吵闹声,才让我的意识本能恢复正常。走出电梯,来到哥哥住院的八楼,我一眼就看见锁子哥紧皱着眉头,站在过道尽头的窗前吸烟,他那黑白相杂,硬挫锉的头发,刺猬一样,一团灰白色的烟雾,萦绕在头上。看见我就扔掉烟头奔过来,说了声回来了,领着我往病房走去。我在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发现他眼睛里满是血丝,像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的样子。这让我本来沉重的的心情,越发沉重。走进病房,哥鼻子上插着氧气,手背上扎着针,闭眼躺在床上。锁子哥说,胡阳,胡星回来了。哥闻声睁开眼,冲我笑了一下。我突然觉得鼻子尖儿一酸,一股辛辣的东西涌出鼻道,嗓子眼咸咸的,叫了声哥,眼睛就红了。哥说别哭,哥没事,扭头让锁子哥给我找凳子,倒水。我在锁子哥递过来的凳子上坐下,拉着哥的手。哥的手瘦骨嶙峋,干硬干硬的,没有一点温度。他的整个人,也干瘦干瘦的,如同一段立死的木头,但精神似乎还好,皮肤比往常白了很多。见我回来,锁子哥开门见山告诉我,哥得的是尿毒症,县城看不了,医院。我说别怕,不管转那里,花多少钱,有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把哥哥的病治好。锁子哥叹一口气说,现在不是钱的事,钱有,你给兑回来的二十万还在。我愣了一下说,那二十万哥哥不是娶媳妇用吗,怎么回事?锁子哥说,打电话给你说有人给你哥说了个媳妇,要修房子交财礼,那都是骗你。你哥得了这病,没钱治疗,一个人忍着疼偷偷在家抹眼泪,是我给他出主意,打电话哄你说有人给你哥说了个对象,女方家要十多万彩礼,还要让修房子。我说为什么要哄我,难道我哥的病,还没娶媳妇重要吗?锁子哥说,你哥不让说,怕你担心,影响工作,所以我就编了这么个故事。你大学毕业没几年,刚刚参加工作,知道这事还不急死,肯定要放弃工作回来给你哥看病。你们家这情况,你能上大学不容易,他不想你半途而废。我说那既然钱在,那就给我哥好好治疗吧。锁子哥说,现在不是钱的事,钱是有了,可没有可以和你哥匹配的肾源啊!医生说,你哥这病,发展到这一步,必须换肾,要不然,人就完了。你钱兑回来后,我就带着你哥来了省城,可我们到这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依然没有等到能够匹配的肾源。再拖下去,可能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哥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亲近的人里找一个血型相符,愿意捐肾给你哥的人,救他的命。你哥只有你一个亲人,把你叫回来,就是希望你能捐肾给他。我听了这话,心里咯噔一下,看着锁子哥愣怔了半晌,没有言语。锁子哥见我不说话,原来充满期望的脸上,眼神变得一片严厉,看着我说,咋了,你不愿意?我望了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的哥哥一眼,走出房间来到过道尽头,掏出根烟点着,透过半开的窗户,望着住院部楼下的草坪。锁子哥跟出来,站在我身后说,你爸妈死的早,是你哥一手把你拉扯大的,没有你哥,就没你今天。他是怎么对你的,你心里清楚,为了你,他都快奔四十的人了,至今媳妇都没说上。他还年轻,你不救他,谁救他?他的话,如同一把铁锤,一下一下敲打着我的心坎。我把烟在窗台上拧灭,扭头看着他问,大夫是怎么说的?锁子哥说,这就是大夫的意思,你哥的主治医生王大夫说,这是唯一的办法,所以我才打电话叫你回来。我说哥,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找王大夫。转过身子,大步往医生值班的医办室走去。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我在锁子哥的陪同下,配合医生抽完血后,把血样送到化验室,等待检验结果。这一夜,我和锁子哥都没有睡,心情沉重陪在哥病床边。能不能换肾给哥,全看明天的检验结果。哥好几次从睡梦中醒来,嘴张着,想和我说什么,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得出他内心的复杂,如同我的内心一样,塞着一把乱草。我想对他说点啥,可我同样说不出来一句话来。漫长的煎熬中,终于等来了天明,医生上班,王大夫把我和锁子哥叫进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验血报告给我和锁子哥说,检验结果出来了,非常不幸,我的血是a型,而我哥的却是b型。也就是说,我和哥哥血型不符,无法配对,所以我不能捐肾给我的哥哥。我听了之后,低下头没有言语,锁子哥却不死心,一个劲问王医生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王医生轻轻摇着头,眼神复杂看了我一眼。我这个时候,身体如同冻在冰棺里一样,连同神经都失去了知觉。那天怎么走回病房的,我不知道,我的脑袋里能记住的,是哥听了这个结果后,脸上那种既像是解脱,又像是绝望的复杂神情。我的躯体,如同被千万只蚂蚁啃噬,被无数把尖刀一刀一刀切割,疼的滴血。“没办法了,该吃吃,该喝喝,让他在最后这段日子走的安详点吧!”王医生叹着气,爱莫能助的声音,一声声在耳边轰响,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哥最后的日子里,陪在他的身边,给他一点力所能及的安慰!日子一天天过去,哥的身体,一天天消瘦,萎缩,逐渐在洁白的病床上,缩成一个刚刚出生不久婴儿的形状,最后,完全消失在了病床上。秋风萧瑟,荒草如堆。埋葬了哥哥后,我没有再到深圳去,每天坐在他坟前的山坡上,望着他坟头上旋转的纸钱,秋风中猎猎飘动的纸蟠,一坐就是一天。哥哥走后,原来虽然陈旧,但却干净的院落,不知怎么,突然就呈现出一副颓废破败的迹象,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了声息生气。院子里,银杏树枯黄的叶片,厚厚落了一层,没有人打理,被风吹着,轻轻旋转;墙头上的狗尾巴草,如同没人要的孩子,匍匐着身子,瑟瑟发抖。我坐在往年这个时候,被哥烧得烫热,如今却冷冰冰没有一点温度的土炕上,秋日的阳光,偷偷从窗户溜进来,静静洒在我的脊背上。光束里,无数的蜉蝣生物漂浮在空中。我的耳朵,在这个时候,变得异常的敏锐,任何微小的声音,都会被捕捉。夜晚老鼠墙角的低语,院子外昆虫的呢喃。那些天,我的神经如同耳朵一样,变得异常脆弱,任何轻微的响动,都会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好几次,我在夜晚和大白天里,听见哥在院子里咳嗽,走动,听见屋门开启的声音。好几次,我看见哥哥走进屋子,在碗架和屋后寻找着什么。院子里,放在墙角老旧生锈的自行车,隔壁堆放杂物屋子里,囤架上儿时玩耍的铁环,每一个物件,都能勾起我一连串的回忆。我的生活,在哥走后,完全陷入一种恍惚无绪的状态里,再也走不出来。岁月在哥走后,变得那么短暂却又那么漫长。有时候,一天昏昏沉沉就无声无息过去了;有时候,却又那么难熬,太阳像是被人用钉子钉在了天空上似的,一动不动。几天后,绵绵的秋雨,开始浸润整个季节,不歇气地一连下了十多天,这个毫无生气的世界,像是浸泡在了水中似的,所有的东西全都受潮发霉,变得如同一团软踏踏的海绵,散发着一股青草被藕泡过的味道。好不容易有一天,风停雨住,久违的太阳从云层里露出半拉子脸,十多天里被雨困在屋里的无法呼吸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站在村街上,三一堆,五一群,议论着这场糟糕的秋雨以及它对今年秋收的影响。我头发蓬乱,神情没落坐在自家大门外的石头上,眼神空洞望着村巷,耳朵里像是听着他们说话,又好像没有。这时候,我就看见锁子哥黑着个脸,手里提着根木棍,怒气冲冲穿过村巷,大步往我这边奔来。锁子嫂呼闪着两只奶子,两手如同鸭子刨水似的,前后划拉着,跟在他的后面,嘴里不知道叫喊着什么。村巷上那些正在说笑的人们,一起停住了嘴巴,嘴大张着,眼睛跟着他们奔走的脚步,一齐扭头往我所在的位置看来。我像是预感到了什么似的,本能地从坐着的石头上站起来,怔怔看着他们,想要返回院里,却挪不动脚。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砰砰乱跳,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在雨后松软的村街上,腾腾踏出擂鼓一样的声响。当这种声音逼近跟前,“啪”得一下,我的脸上就一阵火辣辣的疼痛,眼帘上升起一团黑色的雾霭,我就啥都看不见了。当我的眼睛终于能再次看到事物,我发现,我的身边,不知几时围满了人。锁子哥浑身颤抖,伸展着一只胳膊,手指头哆哆嗦嗦指着我,一张脸如同锅底。我在失去父母,跟着哥哥艰难渡日的岁月里,锁子哥作为村上的村长,家族的能人,和哥哥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给我们兄弟帮助最多,哥哥和我,对他都很尊敬。哥哥病时,是他跑前跑后,医院。在医院期间,我还没回来的时候,又是他一直守在病房,帮忙照顾的哥哥。哥哥走后,见我颓废,他经常过来开导我,给我宽心,有时还强拉我去他家,让媳妇包饺子给我吃。今个他突然来,打了我一巴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啦。这事儿过去很长时间,直到后来,我才从村里人口中知道,原来锁子哥今天的突然愤怒,全是因为前几天晚上他在和锁子嫂和儿子军军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再一次说到哥哥的死,军军不经意的一句话。当时锁子哥说,胡阳那么年轻,才四十岁,媳妇都没有,要是胡星血型和他匹配,他也不会那么快就走了,他真是命太苦了!正在吃饭的军军闻言,停下筷子抬头疑惑看着父亲说,爸,不对啊,医院抢救的时候,是胡阳叔和胡星叔一块帮你输的血,你忘了?锁子哥听了这话愣怔了下,当场就变了脸,看了锁子嫂一眼,“啪”的一声将筷子摔在桌子上,牙缝里挤出一声:“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找他去!”跳下炕就要寻我。是锁子嫂一把拽住他说:“娃他爸,你别急,要问,医院问问医生,把情况弄清楚再说。”第二天,锁子哥就冒着雨,搭车去了省城。医院找到给我哥看病的主治医生王大夫,说明自己的来意,王大夫在他的逼问下,只好告诉他,其实,我和哥哥的血型都是a型,非常匹配,是我不愿意配肾给哥哥,要求医生这么做的,他们也没办法。锁子哥回到村里,拿了根棍子就奔我家来了。现在,他满脸愤怒站在我面前,手指指着我,大声吼叫着说:“胡星啊胡星,你良心让狗给吃了,还是不是个人!你爸妈死得早,是你哥一手把你拉扯大的,他为了你,骨膏熬油,把自己累得跟一个牛一样,为了供你上学,他就差去卖肾了。三十多四十不到,一头的白发,死的时候,媳妇都没说上一个,女人的手这辈子都没摸过!别说他要你个肾,就是要你娃子的命,你都得给,你这么骗他,于心何忍!我,我今个就替冤死的他打死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我怔怔站在门口,在全村人鄙夷的注视下,任锁子哥的拳头棍棒雨点一般落在头上,身上,一动不动。锁子哥打累了,看着一动不动的我,越发生气,轮起棍子还要再打,却被锁子嫂死死拉住。锁子嫂拼命抱着锁子哥的胳膊,大声说,别打了,你别打了,事情已经这样了,胡阳都走了,你就是把他打死,死人能活来吗!“活不来,活不来也要打死这个狗东西,咱们村不要这种没良心的人,你滚,滚!”“滚,滚,滚出胡家村,胡家村不要你这种没良心的东西!”所有看热闹的人,突然振起手臂,冲着我一齐怒吼起来,愤怒的呼声,如雷霆滚过天空,在我的脑袋里轰响。女人们的口水,铺天盖地,如同泛滥的洪水,吐了我满头满身,让我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我在锁子哥和村里人愤怒的吼叫和谩骂声中,缓缓解开扣子,撩起衣服,露出左肋下明亮的,蚯蚓一样醒目的刀疤,慢慢跪倒在大门口,抬头看着天上厚厚的云层,太阳隐藏在云层的后面,如同哥哥的脸,躲在云后望着我笑。我说:“哥,我没有对不起你,爸死的早。你就是我的爸,别说你要我一个肾,你就是要兄弟我这条命,我也不会舍不得给你!可是哥,我没有啊,我拿什么给你,拿什么给你!”滚雷一样的吼声和谩骂声,突然就没了,太阳从云层后探出脑袋,万丈金光,如同无数数不清的长针,刺照在下午的村巷上。空气凝固,整个村庄,如同死光了人一样,静悄悄没有了声息。所有人瞪大眼睛。惊异地看着我,看着我左肋上蚯蚓一样明亮的刀疤。锁子哥举在半空的手臂无力垂下来,棍子落在地上,附身看着我的腰,嘴唇抖了半晌,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怎,怎么回事?”“还记得两个月前吗,你打电话给我说,我哥说了个媳妇,需要二十万块钱?”“记得,咋能忘了。当时你哥病发,一个人躲在屋里哭,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说你哥得的是尿毒症,需要换肾,手术费最低得二十多万,他不想看,想要放弃治疗,是我给你打的电话。”“为什么要哄我?”“你哥不让说啊,怕你担心,没办法,我只好哄你说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女家要十多万财礼,还让修院新房子,需要二十多万。你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好几年了,听你哥说,你在外边混得不错,我想你肯定有钱。”“锁哥,你们以为,考上大学就有前途,参加工作就挣钱了?外面的日子,太难了,这些年,我飘来飘去,哪有你们想得那么好。”“那你哥?”“那都是我哄他的,怕他为我担心。我哥为了我,受了那么多苦,四十了,还没个女人,你打电话给我说他有媳妇了,你不知道我多么高兴,可我哪有二十万给他,为了不使哥的婚事因为没钱黄了,我借不来钱,就把自己的肾给卖了!”“你,你打回来那二十万,是,是卖肾的钱?”“嗯。”“你,你咋不早说?”“我能说吗,我要告诉哥,那二十万是卖肾的钱,我哥还不心疼死了。村里的人知道这件事,谁以后还再供娃娃念书啊!哥,我不是不想捐肾给你,我是没有啊!”我趴在地上,嚎啕大哭,所有的乡亲们看着我,一个个如同木雕。作者简介
万宏,本名鲁万宏,陕西作家协会会员,国内知名青年作家,实力编剧。大量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在全国知名报刊杂志和电台以及网络平台刊登播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五指塬》,院线电影《苹果红了》等。
《陕西作家摇篮》投稿邮箱:shanxizuojiayaolan.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处:网站地址
http://www.sohjm.com//kcyyy/122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