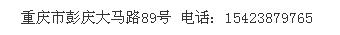
她年轻时受了很多苦。
她出生于军阀出身的穷苦的老中国,在日本侵略和民族危难的黑暗岁月里学习。
她身体虚弱多病,一生常伴有疼痛,她患了股关节结核,终身残疾。他在38岁时做了肾切除术,46岁时得了乳腺癌。
然而她从未低头屈服,她与病魔抗争,经历了三年的高考,最终成为科学家一代,她身强力壮,支持一片天在中国进行半导体物理和表面物理的理论研究。
她是“中国半导体之母”,谢希德。
同时,她也是新中国的首位女校长,也是复旦大学唯一的女校长。
他于出生于福建省泉州一个学者家庭,他的父亲是物理学家谢玉铭。美国的结构在杨振宁的原子结构中称为杨振宁。
为了纪念谢希德,她的最喜欢是她父亲的书房。她喜欢翻阅她父亲书柜里的书,不管他们是否听懂。
久而久之,她对她父亲书柜里的书很熟悉。有一次,她父亲出差,在家里收到一封电报,当时电报局没有翻译电报电码的业务,所以收信人只能自己翻译,因此在家里有一本书,上面有清晰的代码和字符检查。
因为她很匆忙,外婆一时找不到电报本,这时谢希德冲进他父亲的书房,轻松地找到那本书,并帮助翻译电报。
这“成就”使谢希德更加热爱阅读和学习。
进入小学后,谢希德变成了真正的小学霸,第一次考试是一年级。
在卢沟桥事变的影响下,日本入侵军队践踏了华北,谢希德一家携父亲向南逃到贵阳。
不久之后,17岁中的谢希德患上了股骨结核,此时,她刚被湖南大学物理系录取,但因为疼痛不得不辍学。
让她伤心的是,医生告诉她,目前医学水平还没有特效药,她只能回家休养。
这相当于谢希德和“死刑”。
她没有放弃抗争,也从未放下她的书。
她对妈妈说:“读书是我最大的兴趣,只有读书可以使我忘掉病痛,使我的生活充实。读书是治我疾病的良方。”
经过4年的休养,她以顽强的毅力站了起来,自学考上了厦门大学物理系。
谢希德大学毕业,他父亲坚持让女儿出国留学,看到了更大的世界。谢希德参加了美的考试,但她没有考上公费生,只能自费出国留学。
然而当时她家的经济状况无法支撑她高昂的学费,因此谢希德不得不工作,准备明年的考试。
幸运的是,一年后,谢希德被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录取,她是那里的助教,免收学费。
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谢希德收到了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新中国成立了!
谢希德无法控制他的兴奋,“巴不得马上回到中国!”
然而 爆发,不久钱学森被软禁,美国政府宣布,在美国学习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不得返回中国大陆。
谢希德很着急,但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静待机会。
在她等待的两年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
谢希德等不及了,她和她的情人曹天钦讨论了一个策略:谢希德逃离美国,结婚英国,然后归国。
谢希德一上开往英国的船,美国的警察就来了。经过盘问和盘问,他们发现谢希德行李,只有几千封带有曹天钦的信件必须放行。
回国后,她来到复旦大学物理系任教。在复旦中,她开设了七八门基础课程,如光学和理论力学。每次开课,她都会把他交给其他老师,开新课。
同时,她看到电脑是由电子管组成的,占据了很大的面积。因此她敏锐地意识到半导体科学将改变未来的计算机科学,从而改变她的研究方向,并致力于半导体物理的研究。
国家想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人才储备库,希望谢希德可以担任北京的副局长,主持工作。
那时候,她的儿子刚出生,就在大家都以为她会要求离开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干脆收拾好包裹去了北京。
两年后,她和黄昆合作编辑《半导体物理》问世,开创了中国半导体领域的先例,长期以来,本书已成为我国半导体物理专业的标准教材和基本参考书。
与此同时,第一个单晶硅,第一个半导体材料和第一个晶体管也在她的努力下诞生。
此后,国家许多高校设立了半导体专业,为半导体材料和器件建立了研究所和车间。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使谢希德无法进食,有一次,她在实验中突然晕倒了,后来,人们知道她因严重肾结石和心脏病工作了近一年。
在手术后之后,她又站在站台上。好时机并不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她从事体育运动,她住在牛棚里,干苦力,打扫厕所和其他脏活。
后来,在这种情况下,她被发现患有乳腺癌。
虽然这种病对她不利,但她从未放弃过自己。
在她小小的身体里,有着巨大的能量。
在,谢希德成为新中国高校的首位女总裁。
作为校长,她眼光长远,眼光敏锐。她率先打破了中国综合性大学文科和苏联模式,她又增加了几所学院,如技术科学、经济和管理,把复旦变成一所综合性大学,拥有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
她还打开了刚刚诞生于国际上的表面物理学,并成立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以促进中国学生理解美国。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出国,谢希德坚持下班后给世界高校写推荐信。只要她被谢希德认出,不管她是不是学生,她都会写一封长长的推荐信。
谢希德对陈词滥调、毫无根据的空谈极为反感,每封推荐信都是真实而全面的。
“虽然这要占用我不少时间,但对我是一种乐趣。”
还有一次,一个学生刚从德国回来,想搞一些科研项目,却没有资金支持。他请他的导师谢希德写一封推荐信。
那时候谢希德刚刚去世,他想找其他老师写一封推荐信,令他惊讶的是,追悼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谢希德给学生们发了推荐信。
学生们很抱歉,但是“其实,信让我自己起草,您审定签个名就行了。”谢希德说:“由我亲自来写,对你更有帮助。”
在担任校长期间,复旦大学参加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外国媒体记者致电她“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
在她晚年,她的癌细胞转移到胸壁和淋巴结好几次。她的胸腔积液很严重,将近2万毫升的胸腔积液被抽取了29次,相当于40个盐水瓶的容量。后来,她不得不插上几根管子,氧气,鼻饲,输血,插管,然后是心脏监护仪。因为腿有残疾,卧床休息也是被迫的姿势,无法右侧行走,让她非常痛苦。
谢希德却非常强壮,从不打鼾。
当她还能说话时,她对每一个帮助她的医护人员说:“谢谢”。即使插管到了喉咙,再也说不出话来,她还是轻轻地捏着医护人员的手,表示感谢。
医生说,“我们从未看到这样有风度的病人。”
在她住院期间,她唯一的要求就是一部电话把她和电脑连接起来。因为她的腿不能弯曲,她不得不站起来工作。每天收发大量邮件,处理很多事情。直到发生急性心力衰竭和呼吸衰竭,抢救,再也站不起来了,只能停工。
负责治疗她的医生说:“她近10次心衰后,医生在抢救中给她插了呼吸管。她醒来后希望把插管拿掉,在我手上写了一个‘死’字,她要在最后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向她解释,照现在情况呼吸机不能拿,只有一个可能是从颈部切开气管。没想到她立即表示同意。”
医院死亡。她在遗嘱中写道:“把我的遗体捐给中国医疗事业。”
当晚,从复旦物理系9号楼一直延伸到第一教学楼,数千只学生自发折叠的纸鹤布满树枝。
很多人还记得,在他去世前,谢希德参加的最后一次教师节晚会,谢希德和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并肩站在宽阔的舞台上,台下坐着全市教师代表和青年学生。
当主持人问她:“代时,是什么力量使您冲破了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谢希德对着麦克风说:“我、爱、中、国!”